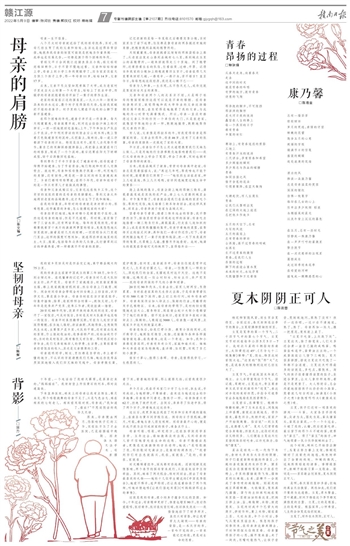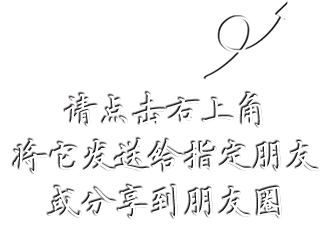□张文锋
母亲一生不容易。
八个月大时母亲被送给了我的祖母抚养,当时,祖母已经生育了我的父亲和姑姑,生活也是过得非常拮据,她抱养我母亲的初衷可能就是把她当作童养媳——此举也是实属无奈,一切都是源于那个困难的年代。
曾祖父平日会到桃江边捕鱼卖点小钱,祖父祖母则租田耕作,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父亲和姑姑相继上学,母亲上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因为家里实在无力供三个孩子上学,那一年母亲11岁,姑姑14岁,父亲17岁。
后来,父亲不负众望如愿考取了大学,成为老家村子里走出大山的第一个大学生,姑姑上了农业中学,而辍学的母亲跟随着祖母开始了一辈子的劳作生涯。
老家的祖屋在江边的围屋里,一九六六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过后,整个村子变得荡然无存,包括我家破烂不堪的老房子。村子里的人便在不远处的山脚下重新开基建房。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建房子并不是一件易事。每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要早起,到河边去拾捡沙滩上的河卵石,一担一担地挑回宅基地;上午、下午参加生产队出工干农活,中午利用劳动的间隙去后山砍木料;晚上借着月色做建房用的泥砖,从挖黏土,做砖坯,每一道工序都洒下母亲的汗水。特别是没有牛,就用人力代替牛劳作,靠自己的双脚踩踏搅拌黏土,再把黏土放置在专门的砖格里,制成了一个个泥砖,最后还要在阳光下晾晒成型,晾干后再搬回宅基地。
等到费尽了千辛万苦备足了建房材料,祖母就请了师傅开始建房,为了节省资金,她们轮流和村里人交换劳力。就这样,母亲和祖母像燕子筑巢一样,利用她们的肩膀,还有韧性,硬是把一排五间的砖瓦房建起来了。乡亲们都啧啧称赞道,在那个年代,母亲和祖母干的是一件只有男人才能做成的事情。
母亲和父亲成婚以后,父亲还远在他乡工作,这个贫穷的家依然靠的是母亲的肩膀撑起。等到父亲从外地调回老家的县城教书,这才先后生下了我和妹妹。
在我的印象里,年轻时的母亲就是身材娇小的,很难想象,这样羸弱的身躯,怎么能撑起家的大梁?
母亲经常打趣说,她身材矮小是被重担子压的,虽然这是母亲的趣话,但是不无道理。那时候,家里除了种了三亩水田,还有两亩旱地。每年的夏收秋收,母亲都要挑着百十来斤的满满两箩筐的稻谷,晃晃悠悠地从田里挑回,接着是好几天的晾晒,一担担稻谷从门里进门里出,这样的强度可想而知。就连那些种在地里的花生、大豆、高粱,包括每年必养的几头猪,从打猪草到以后的种桑养蚕,哪一样都离不开母亲的肩膀。
记忆犹新的是每一年夏收之后都要交售公粮,当时家里为了省下运费,往往都是靠母亲的两条腿还有她的肩膀,把粮食挑到县城的粮管所的。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挑着沉甸甸的两麻袋稻谷上路了,从老家出发走山路到县城有七八里,再到城北五里山的县粮管所,一趟来回就得走三十里地。到了粮管所,还要排着长长的队伍,忙着验质、过磅、开票。记得当年我家的公粮加上购粮就要四五百斤,母亲在那几天里要来回好几趟,一路艰辛、一路汗水,苦不堪言!直至今日,每每想起这段经历,我还是心酸不已……
母亲为人和善,一生乐观,从不怨天尤人,或许这就是客家妇女天生的秉性。
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只是碍于祖母的情面而维持这段可以说是不幸的婚姻。在母亲的潜意识里,就觉得她和我大学毕业的父亲这场婚姻实属不般配,甚至觉得是她拖累了我的父亲,为此她的内心时常充满着愧疚。所以,母亲一直没有踏进过父亲工作的任何一个单位的大门,只是在老家,就像坚守阵地的士兵一样,默默地操劳,默默地等待我父亲的归期。
有人说,父亲像是那拉车的牛,而我觉得母亲是那撑家的梁。父亲去世那年,母亲46岁,没有了父亲的依靠,母亲的肩膀再一次挑起了家的大梁。
平日里,母亲似乎不怎么用大道理教育我们兄妹怎么做人,只是用她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我们从母亲的身上学会了宽容、学会了执着,同时也拥有了母亲那样的秉性。
后来,我在县城买了新房,常常劝母亲离开老家,母亲总是笑着摇摇头,说:“再过几年吧,等我啥也不能干的时候,就需要你们照顾了……”她依然生活在老家,种上几畦菜地,养上几只鸡鸭,安详闲逸地度过她生命中的黄昏……
逢上县城的集日,母亲会骑上她的那辆三轮车,满载着蔬菜或是其他的农产品,骑上七八里路到城里去卖。中午集市散了,母亲就会进我们在县城的家里吃个饭,等到吃完饭,她又踏着三轮车匆匆回去,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母亲奔波于老家与县城之间。
望着母亲弓着背,蹬着三轮车远去的背影,我不禁潸然泪下,脑海里经常会浮现起这样的画面:母亲吃力地踏着一辆三轮自行车,满载蔬菜,行走在人流如织的路上;或是在熙熙攘攘的集市,母亲守着她的菜筐,在等待买主的驻足问津,再和他们一番讨价还价;灯下,母亲照例掏出她用了一辈子的塑料钱袋,把一天下来卖菜所得的角票、元票数上几遍,整整齐齐地叠好。此时,她满头的银发在昏暗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