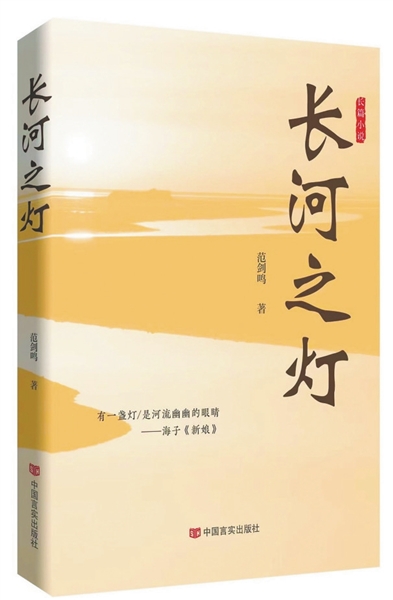□何树兰
《寻梦环游记》中有一段经典台词:“据说人的死亡有三次,第一次是生理意义上的死亡,第二次是法律意义上的死亡,而最后一次,是当所有人都忘记你了,那么你也就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所以,死亡不是一个人的终点,遗忘才是。基于此,《长河之灯》在记忆轰然倒塌的声响中听见了“泥土”的诉说,抓住了一个个梅江边的身影,使那一砖一人的往事在这纸上鲜活起来。小说《长河之灯》借助“讲古闻”这一民俗形式讲述了小脚女人灯花守护家族发展壮大、兴旺至今的故事,记录了梅江人家的奋斗与悲欢,展现了重情重义、吃苦耐劳的客家精神。
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认为,一个文本总会同别的文本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在它以前的文本遗迹或记忆的基础上产生的,或是在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中形成的,总会与前人或同时代的人的思想或话语发生种种直接或间接的文字关联。《长河之灯》追溯的是一百二十多年前血脉长河最初的一滴水的流淌,主要写了三代人的故事,以“青砖”为线索,记录了梅江边一户普通人家的奋斗与发迹。而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制”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同样是一部“家族史”,讲述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书中有两次明示了两本书的关联,第一次是祝独依初闻“讲古闻”的民俗,她想“她在马尔克斯笔下领略过马孔多的神秘”“难道梅江边的小镇,也有个神奇的布恩迪亚家族?”,对这场“民间奇葩”充满了好奇;第二次是祝独依亲临“讲古闻”的现场,她充满疑惑,只是“她忙于记述这种‘讲古闻’的民间奇葩,就像当年迷醉于《百年孤独》。”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百年孤独》的熟悉和欣赏。从全局来看,《长河之灯》也处处透露着《百年孤独》的影子。
首先,是人物的互文。《百年孤独》中有一位贯彻始终的人物——乌尔苏拉,她一直活到自己的第六代出生,在暮年完全失明仍掩饰,继续自己的操劳和回忆,她是布恩迪亚家族能够延续的支柱,是所有人的母亲和长辈。随着孤独而伟大的乌尔苏拉告别世界,马孔多小镇也不可逆转地沉沦下去。《长河之灯》的灵魂人物也是一名伟大坚韧的女性——灯花,看船的灯花和奋力追赶散排的有财曾有过一面之缘,但真正的缘分开始于灯花新婚丧夫,书苗为有财说亲,至此一个家族的雏形出现。她历经丧夫之痛,穿过跌宕起伏的时代风云,长寿地看着“不同辈分的妇人,不同年代的妇人,不同村落的妇人,聚到了一起”,编织成一个越来越大的家族。和乌尔苏拉的晚年命运不同,灯花并未遭受小辈的愚弄和冷落,而是在浓浓的亲情中体面地离世。马尔克斯认为“妇女是使世界不致毁灭的支柱,而男人则没法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乌尔苏拉是布恩迪亚家族的始母,她是理性的象征,具有女性几乎一切的优点。而灯花的舞台更多圈囿于对家庭的贡献,她守寡半生,为一大家子操劳辛苦,是梅江边驰名的有德之人。
其次,是主题的碰撞。《百年孤独》讲述的是马孔多小镇和布恩迪亚家族的兴衰变化与传奇故事,记录了家族命运与百年历史。《长河之灯》也是一个关于家族的叙事,二者却略有不同。马尔克斯是通过讲述布恩迪亚家族的故事,刻画人物殊途同归的孤独命运,进而体现出个人、家族及全人类的悲悯与孤独情怀。而作者关注的是普通百姓那随风扬逝、隐入尘埃的小人物的一生。书中一段话这样写的:“国史是大人物的事,记的都是轰轰烈烈的历史,而普通百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多少人默默无闻,生死轮回,每个人从哇哇大哭开始入世,最后就成了族谱上一个名字,或一块墓碑(甚至连墓碑都没有),成为人类长河中一个无足轻重的节点,所有的悲欢离合都抽离失佚了。”简言之,在《百年孤独》里,我们读到的是整个人类难以摆脱的无意义感与孤独宿命的纠缠,但在《长河之灯》里,我们观照的是自己琐碎的、微不足道的人生。
最后,是技巧的借鉴。《百年孤独》的末尾,奥雷里亚诺终于参透了梅尔基亚德斯羊皮卷的奥秘——“梅尔基亚德斯并未按照世人的惯常时间来叙述,而是将一个世纪的日常琐碎集中在一起,令所有事件在同一瞬间发生”,原来卷首提要“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早就写好了这个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的命运。命运的写手马尔克斯把未来、过去和现在三个时间层面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用独创的从未来的角度回忆过去的新颖倒叙手法演绎着这场传奇,在回忆中随意支取时间的片羽(标志词“多年以后”),提醒读者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单线旅程。《长河之灯》则巧妙地借助了说书的形式,利用听故事的人发表意见,反复拉回时间线,打破了平铺直叙的叙述。这造成一种“戏中戏”的感觉,我们在看一群人听故事,我们是听众的听众。作者为我们转述了过去的故事,并借祝独依和敦煌等人之口发表评论,因此,我们不仅听见了故事,还听见了听故事的人的看法。这些“弹幕”输出自己的观点,也引导我们双重思考——灯花的命运走向会是怎么样的?这些婚姻观争论是否都有问题?美中不足的是独依和敦煌等人的议论有时出现得太过突兀,使读者沉浸感不强。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作家所表现的历史真实,也许比任何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家都要多得多,因为它更具体、更贴近生活。”谁敢说,灯花不是亿万母亲的缩影呢?谁又敢说,当代年轻人没有着像独依和薪火一样的挣扎和恐惧呢?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我不过是想点亮一盏文字之灯,照见乡亲们的生老病死。我不过是想让亲人们像一块块土砖,再次在纸上站起来。”是的,他做到了,读者在这本书里看到了这滴血脉源头的流淌,看到了灯花对时代的消化,看到了那个年代“多记恩,少记仇”的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