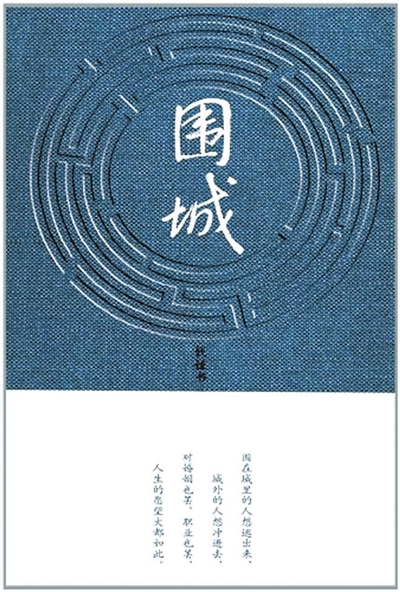□李伟明
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拍成电视连续剧而出名。此后,作为学者的钱锺书,曾经被推到文坛前沿,万众瞩目,如日中天,掀起过一股“钱锺书热”。那时我正上高中与大学,《围城》的男主角方鸿渐常被同学们提起,“克莱登大学”常被拿来当笑料,钱锺书的奇闻逸事开始不绝于报刊,他甚至因为纯粹的学者形象而在校园成了偶像级人物。
惭愧的是,电视剧《围城》热播的年代,我并没多少机会看电视;而小说《围城》,在乡下时也是不容易看到的,待得进城后有机会看了,又因为找一本书不再难,觉得要看的话随时可看,结果也是一直没有像样读过。
现在,工作更紧张了,想做的事反而越来越多。在忙碌中,近日总算抽空把这本久仰几十年的作品看完了(读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2月第2版、2022年1月第45次印刷的版本)。
一本书,只有从头到尾读完了,形成的印象才完整些。要说《围城》最大的亮点,我觉得还是体现在语言上。故事本身未必有多精彩,但它的表达方式,相信读过的人都会难以忘却。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我甚至感到作者不是在写小说,它几乎通篇洋溢着浓郁的讽刺与幽默,让人读出满满的杂文味。
因为语言的风趣,这本书读着有味,时常可以让你面对文字报以一笑(包括苦笑)。比如第一章写方鸿渐向远在美国的骗子购买“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利用小聪明把骗子给耍了一通,作品中写道:“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一句话简直把近代中国的屈辱史活生生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你体会到什么叫“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方鸿渐与同船的鲍小姐去西菜馆吃饭,“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间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真是极尽夸张之能事,读了令人忍俊不禁,感叹生活可以荒诞若斯。在第二章,方鸿渐留洋回到家,方父与他聊天时说道:“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男人非比她高一层,不能和她平等匹配。所以大学毕业生才娶中学女生,留学生娶女大学生。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有洋人才敢娶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与此异曲同工的还有第三章写到曹元朗的心理活动时所说的:“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这些绕口令般的诙谐,成就了一段经典语录,又让人突然无语。
就是描写外貌,作者也不忘调侃一番。第三章唐晓芙初亮相,作者写道:“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瞧这根刺长的,简直让人想起仙人球。而第六章分别描写陆子潇和韩学愈的外表时,有些用语则让人脑洞大开。韩学愈讲话时,“这喉核忽升忽降,鸿渐看得自己喉咙都发痒……恨不能把那喉结瓶塞头似的拔出来,好让下面的话松动。”如此观察、如此笔法,真是古今中外独此一家。
《围城》写到的人物当中,几乎没什么传统意义上的正人君子。在作者笔下,对他们的揶揄比比皆是。第六章开头写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说他是研究昆虫的“老科学家”,然后冒出一句“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这个校长是什么样的人,几句话就让你知道了。而且这个高校长信口胡扯的话,因为大家“倾倒不已”,“经朋友们这样一恭维,他渐渐相信这真是至理名言,也对自己倾倒不已”——所谓“大人物”之所以自我感觉良好,不就是这样来的么?被违心的奉承话“捧杀”的小人物,在我们身边只怕也不少见。同样出身于“克莱登大学”的韩学愈“博士”,自称“著作散见于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中”,但高松年校长不知道的是,他的作品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的人事广告栏和《史学杂志》的通信栏。以前我们调侃某某“作家”发表的文章是报缝的《征婚启事》,没想到钱先生早就想到这点幽默了。
小说本以讲故事为主,《围城》好议论的风格却随处可见,作者常在不动声色中针砭时弊。比如书中第六章说,“一切会议上对于提案的赞成和反对极少是就事论事的。有人反对这提议是跟提议的人闹意见。有人赞成这提议是跟反对这提议的人过不去。有人因为反对或赞成的人和自己有交情,所以随声附和。”一笔就把某些人的无原则心态道破。第七章说汪处厚被人弹劾,官做不成:“亏得做官的人栽筋斗,宛如猫从高处掉下来,总能四脚着地,不致太狼狈。”从这些表述不难看出作者对当时官场的态度。书中又说“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某些文人的酸样呼之欲出。读至此处,不禁想起很多年前某单位一位粗通文墨、爱写“打油诗”的老先生,每当有人去世,他便要在单位内部小报的报缝发表悼念诗。于是,我们一看到他的大名出现在报上,就条件反射般地想到最近定然又有谁仙逝了。第九章写方鸿渐回到上海要找房子住,“房子比职业更难找……上海仿佛希望每个新来的人都像只戴壳的蜗牛,随身带着宿舍。”看来,“蜗居”的说法,说不定来自钱锺书这里。整部作品读下来,创意多多,妙语处处,别开生面,妙趣横生,极大地弥补了情节的不足。
钱锺书的主业其实不是写小说,而是钻故纸堆。这种学者,一般来说,给人的印象是迂腐古板,不谙世事。然而,读了《围城》就知道,作者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世事洞明,对人情世故一直看在眼里,识在心里呢。作品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精彩,让人觉得作者识人真是“贼精贼精”。比如第六章写高松年违背承诺,将方鸿渐从教授改为副教授时与方鸿渐的对话,其“老江湖”的形象立时鲜明起来。方鸿渐想着要不要把自己带的教科书公开或油印给学生,最后决定还是不必,“万不可公诸大众,还是让学生们莫测高深,听讲写笔记罢。”寥寥数语,让人感到象牙塔也是处处皆“心机”。而刘东方教授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教鸿渐对坏卷子分数批得宽,对好卷子分数批得紧,因为不及格的人多了,引起学生的恶感,而好分数的人太多了,也会减低先生的威望”。这大概也算是“精致利己主义”的表现之一吧。看看某些知识分子,把一肚子的聪明才智都用到哪儿去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通过人物性格的描写,可知作者在生活中应当不是无趣之人,他对人性读得太烂熟,把生活看得太透彻。
《围城》在读者当中的风评极好,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同时代最好的小说,至少从可读性的角度来说是这样。这些观点当然未必权威,我倒是觉得,作品的故事谈不上特别曲折特别深刻,反映的内容也只是局部的、微观的,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甚至难免以偏概全,但因为语言的辛辣别致,让人感到有趣,于是把故事的不足给忽略了,只记到了它的好,而忘记了它的缺陷。小说夹带杂文色彩固然不是坏事,但在情节铺陈上,还是应回归“故事为王”,过于直露的“杂文笔法”一旦用过了头,或将反噬作品的艺术性。每种文体都有各自的“技术标准”,对小说而言,一味在语言上炫趣,有时可能喧宾夺主,消减了作品的容量,我还是更希望它能延展更多的情节,关注某个时代更多人的命运。
除了故事让人不过瘾,段落太长也是个问题。不知何故,作者经常一个大自然段讲述太多的内容,有些段落转折了几个点,完全可以分成多个自然段,但作者偏要一口气写下去,在一定程度上给读者带来阅读的不适感(如第二章写方鸿渐演讲之后的事,再到方家迁到上海躲战乱,跨度几个月时间,其实是几个层面的事。而第七章写方鸿渐与孙小姐订婚则来得太突然)。至于章节的篇幅也太长,没有间歇,容易使人产生阅读疲劳。
最后提一笔闲话:《围城》也有“赣南元素”——提到了宁都县。第五章写方鸿渐一行从上海去湖南三闾大学任教,旅途艰辛,“车下午到宁都”,然后用了两段写他们在宁都的生活情景,可惜在这里吃住都很狼狈,难免让今日宁都乡亲感到几分遗憾。随后,一行人一顿争论之后,向吉安去了。据考,钱锺书途经宁都实有其事,当年他本人便是基本按这条路线从上海去湖南任教。不管怎么说,这些地名能被实名制写进小说,随着作品的闻名而被更多的人记取,也算一件小小的幸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