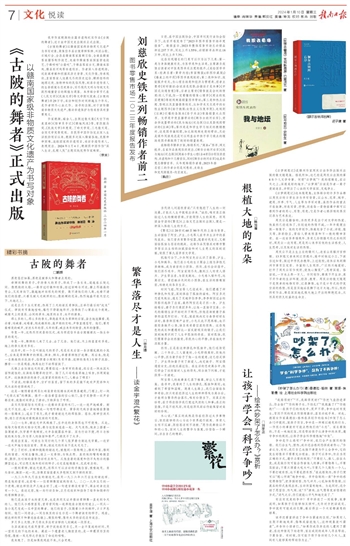□朝颜
黑夜苍茫如幕,黑夜是被香火和舞者点亮的。
举狮而舞的男子,手持香火的男子,形成了一条长龙,逶迤在丘陵之间。像燃烧的火焰,一路穿过圩镇和村落,经过田畴与河流,攀上那高高的青山,又反身向下,激越地冲向祖先的祠堂。数不清他们的人数,也看不清他们的脸膛,只看见被火光映照的红,像斑斓的花朵,热烈地盛开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
这是正月十五元宵夜,热闹了三天的谢氏蓆狮队,正举行最后的“赶龙”仪式。锣鼓有节奏地喧响,爆竹不停歇地炸开,仿佛铁了心要在这个夜晚,喊醒天上的星辰、山间的草木、地里的虫豸、水中的游鱼。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香火,奔跑在双龙与蓆狮的后面,奋力地追撵着、晃动着、呐喊着、吆喝着,构成雄浑的、高声部的交响,声势直透苍穹。他们,要用最嘹亮的喊声,宣泄头年的苦、头年的累,喊出来年的盼望、来年的憧憬。
年复一年,这热烈而欢喜的仪式,成为照进信丰县古陂镇谢氏一脉生命里的亮光。
年复一年,舞狮的人来了又去、去了又添。他们说,天上的星星有多亮,地上的香火就有多旺。
这其中,有一个名叫谢达光的男子,先是长龙后面一条活蹦乱跳的小尾巴,后来是蓆狮舞中的狮尾、狮身、狮头,举着蓆狮粗犷起舞。再后来,他是一名熟练的乐队鼓手,指挥着小廻廻(负责开路、逗狮的角色)为狮子洗脸、擦背……但是现在,他再也打不动那面鼓了。
从镇上去往谢达光的家,需要经过一条窄窄的巷道,然后是一块水泥大面积剥蚀的、长满铁马鞭草的空坪。除了几只母鸡在草地上啄食,四周阒寂无声。这挨挨挤挤的房子,这紧紧闭锁的大门,人都去了哪里?
不消说,村镇深巷中、空旷旧屋里,留下来的多是激不起欢声笑语和大风大浪的老弱病残了。
这是一幢附着在两层红砖屋旁的低矮水泥砖简易建筑,门楣上,钉一块“光荣之家”的牌匾。推开一扇漆着蓝漆的空心铁门,屋子里静得一丝声音都没有,就像时间停止了游动,万物屏住了呼吸。
县文化馆副馆长刘荣生一边推动里屋的木门,一边一迭声地喊着。谢达光不支应,连一声咳嗽或一句嗯哼都没有。黄昏的光线吝啬地铺在靠墙的一张矮床上,适应了很久,我才看清谢达光的那张脸。苍白,眼神空洞无物,眼仁茫然地对着爬满灰斑的天花板。
二〇一七年,谢达光中风瘫痪了,左半边的身体再也不听使唤。从此,他每天每夜的大部分光阴,都与这张床连在一起。天气炎热,他身上搭着一条薄被单,仅穿着平角裤衩,大半条腿露在外面。因为行动不便,终日与枯寂的床为伍,作为男人的体面和尊严,已顾及不了太多。
我退出里屋。刘荣生与同行的几个男人张罗着为谢达光穿戴,一边穿一边大声地与他拉家常。原来,谢达光的耳朵不是太灵光了。
穿上了衬衫、长裤和拖鞋的谢达光,被抱到一张轮椅上,推到外屋,推到我的面前。刘荣生懂他,递上一支香烟,为他点燃。虽然他的嘴角略微歪斜、颤抖,但叼烟的姿势仍旧有点帅气。从他坐着的高度和仍不失粗壮的胳膊望过去,可以想见他年轻时的样子,必定是魁梧高大、孔武有力的。
一提到蓆狮,谢达光就哭,用那只可以活动的手掩住面,嗷嗷地哭。肩头耸动,胸腔一起一伏,仿佛里面装着太多想倒又倒不掉的东西。
一九三六年九月出生的谢达光,在哭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生的谢达祥。那是他的堂哥,此前唯一一位蓆狮舞国家级传承人。二〇一九年五月的一个夜晚,谢达祥悄没声儿地去世了,连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离去时身边没有一个人。在这之前,他一向行动自如,正月还组织和指导了每年如期举行的蓆狮舞活动。
他们是血浓于水的堂兄弟,也是共同见证并推动蓆狮舞一直走到今天的人。他们从小感情甚笃,堂哥曾同他一起奔跑在古陂的村道上,一同从一条小尾巴变成一名中坚的舞者。他们的屋子,仅隔着小半块晒坪,日日声息相闻。他们一同老去,一同为族里的后生示范一个舞者该有的样子。现在,谢达祥的照片和事迹挂在墙上,微张的嘴,像有太多的话还没有说出。
岁月多么无情,岁月将太多没有活够的人封缄成一段历史。
与其说谢达光在哭堂哥,毋宁说他在哭自己,哭一去不复返的时间,哭一望而见的不远的未来。藏在一个耄耋老人胸腔里的,是一种覆顶而至的恐慌,像被一双无形之手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我来晚了。但是如果我现在不来,只会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