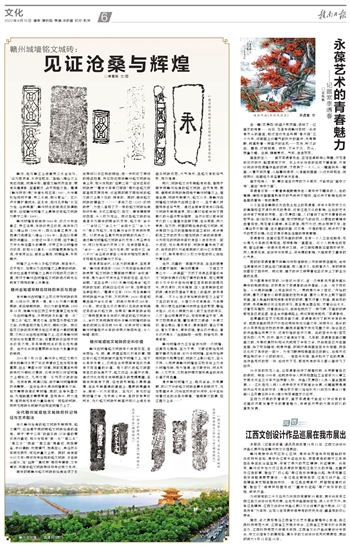□王先桃
在一幅《花瀑图》的盛大繁茂里,读到了一位画家的诗意……近日,笔者走进赣州老城一条深巷尽头的画室,越过启功先生所题“春云阁”三个大字,迎面碰上这幅气韵恢宏的画作,光是题眼,就蓬勃着一种盎然的生机——花鸟,呼之欲出。墨色,打破樊篱。枝叶,不浮不浅。花头,层叠交错。空间,肆意豪放。气势,浩浩荡荡。
画室的主人——画家李遇春先生,正站在桌前凝心挥墨,对笔者的突然到访,略显局促不安。纸上光彩夺目的他却不善言辞,只有谈到创作和满墙作品的时候,才像换了一个人,从一幅画到另一幅画,从喜欢到执着,从临摹到速写,从油画到国画,从过去到现在,侃侃而谈,话里话外洋溢着热爱与自信。
画家和诗人一样,需浓缩自然界的万千美好,才能写出“画中之诗”,画出“诗中之画”。
李遇春这样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走在人群中并不醒目的人,他的腼腆、谦和与画里蓬勃奔放的气质并不相符,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品里透着诗一样的情愫。
从小生活在赣南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李遇春,深受千年历史文化的熏陶和客家淳朴民风的浸染,还有红色文化的影响,让他的艺术创作有了别样的灵感。在《花瀑图》里,人们看到了他艺术青春的刹那芳华;在《白羽戏清溪》里,那对振翅欲飞的白羽,以朦胧的意境冲击着视觉,用笔看似简单,其实很难,用巧太过,就会用神不足;在《情绕紫云烟》里,在水墨韵致里,仅仅是一只猫的憨态,就点燃了春天的繁花似锦,这应该是平常生活里的寻常意境。
李遇春说,在画这些花鸟画的时候,总有一个人立在他脑海,无论是几十年前还是现在,那种影响一直都在。这个人就是他的老师、曾经的赣一中美术老师许又硕。许又硕和傅抱石曾同校学艺,两人是表兄弟,在创作与布局上,深受傅的影响,大胆探索又富有时代气息。
那时的李遇春喜欢到赣州市标准钟叔公开的钟表店里玩,途中经常看到许又硕坐在门前画画,那人画多久,他就看多久,有时候连饭都忘了回去吃。就这样,惜才的许又硕带着他正式走上了职业绘画的生涯。
努力都是有收获的,20世纪90年代,在一次电影优秀宣传画比赛中的脱颖而出,彻底激发了李遇春的创作潜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兴趣到临摹,从写生到修为,一晃就是大半个世纪。“开始的时候,喜欢对着叔公钟表店里的老物件画,喜欢从报纸上剪下插图来画,画火柴盒封面和电影海报的时候,喜欢对着人物画,再后来的时候,走进赣南这片土地的深处,甚至是全国各地,对着山山水水,对着花鸟植物,对着湖泊山川,渐渐地就成了一种习惯,不画的时候感觉自己很空虚,在业余作画道路上,就这样越走越远。”李遇春说。
在厚重的客家文和西洋画之间,李遇春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尝试,把西洋画的技法巧妙地运用到传统绘画之中,利用光线、色彩的浓淡来表现出动物的传神,融西洋画理于传统笔墨之中,除让自己的作品雅俗共赏之外,还有朴拙的自然之美。他的百米长卷《百花百鸟图》,大气,恢宏,画外之音绵延不绝。几年前,李遇春在画这幅画之前,光是收集材料和采风就用了半年之余,然后把自己关在画室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作画,时间仿佛凝固在百米长卷里,而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为练习眼神和稳固自己的耐心,他每天还要坚持打半个小时的游戏。一卷百米长卷,差点耗光了他的激情,当作品完成的那一刻,他说放下笔,感觉所有的鸟儿都从画中飞了出去。
50多年的执笔人生,让李遇春创作了辉煌成就,也贡献着自己的虔诚。早在1990年,他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评为从事工艺美术行业三十年杰出贡献人物。作品《花瀑图》入选八届全国美展,《一江秋色无人问》入选泰中艺术家联谊会会展,这幅画更是得到关山月先生的好评,《情绕紫云烟》《灿灿秋光》《白羽戏清溪》《春宵》《名花夀石共千秋》等分别获得国家级奖项。
正因为对美的执着追求,画家李遇春才能在83岁这样的年纪里依然散发着艺术的青春魅力,传递自然界的大美与时代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