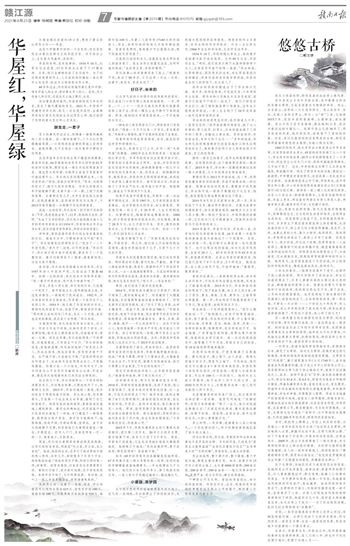□朝颜
从瑞金城往东南约15公里,便到了著名的红军烈士村——华屋。
这是叶坪镇黄沙村的一个自然村,村庄里世代生活着以农耕为主的华姓子孙。村子的后山上,生长最为茂盛的,是松树。
华屋的松树,是有故事的。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17位华姓后生栽下了17棵松树。后来,他们全都牺牲在了长征途中。为了纪念那些英勇的烈士,人们在松林间建起一座红军烈士纪念亭,把这片小树林称为烈士林。
80多年过去,所有的壮怀激烈都已复归平静。唯有华屋人的生活,牵动着太多人的心。是的,烈士的亲人和后代,还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沐浴着发展的春风,华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我又一次走进华屋村,去看看那里的红军后代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他们经历了怎样的重大变迁和心灵洗礼。
跟党走,一辈子
夏日的熏风穿过后山,轻拂着一幢绿阴掩映的二层小楼房。在一楼的房檐下,三个大红灯笼微微摇晃着,一只母鸡则在屋侧的草地上安闲啄食。放眼周遭,无不呈现出一派朴素而宁静的乡村图景。
这是华屋专为村里的五保户建造的保障房,房屋共四套,94岁高龄的老党员华从柏和他92岁的老伴刘桃秀,便居住在一楼左手边的那套房子里。透过宽大的纱窗,刘桃秀正在屋子里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华从柏从里间慢慢挪出来,一边对老伴说:“好啦,你就少说两句吧。”原来,刘桃秀年纪大了,脑子已经有些糊涂。而华从柏最近几年开始腿脚不便,走路只能一步一挪,上坡下坎都很艰难。夫妻俩没有儿子,大半生居住在土坯房里,没钱改建新居,直到被村里列为五保户,于2015年春节搬进一分钱都不用花的新房里。
说起一生的经历,华从柏有一肚子倒不完的苦水:“7岁,我爸爸就去世了;12岁,我妈妈又去世,苦啊。”失去了父母的荫护,华从柏只能跟随大他十几岁的哥哥华崇松生活(1934年,华崇松响应号召去当红军,在长征途中受伤掉队,伤好后回到华屋)。
穷和苦,曾经是烙印在华从柏生命里最深刻的记忆。瑞金方言中,习惯将单身汉叫做“单尺子”。华从柏便是这样调侃自己:“我当了一二十年老光棍,‘单尺子’,没钱,讨不到老婆。”年近四十,华从柏才经乡亲介绍成婚,算是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妻子刘桃秀是个二婚亲,最重要的是,讨这头亲不要钱。
在华屋,华从柏是党龄最长的老党员,自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过去了整整64年。回顾一生的经历,华从柏至今仍觉得自豪:“我一辈子听党的话,党叫我干啥就干啥。”
其实,早在入党之前,华从柏的行动,已经像一个党员了。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投身土改,当过民兵排长,一路做到了民兵连长。1952年,华从柏在村里当互助组长,负责着一个组四五户人家的工作。1954年,他又做了华屋初级社社长,带领村民到田里干活,安排下种,管理田间作物。“那时候工余时间专门开会,反正一个光棍,家里也没别的事做,我总是十分积极。”华从柏说。
大集体时期,华从柏在村里当小组长,记工分。有时工作也不好做,比如村里有个妇女,大家都怕她,每次出工都是最后到,还振振有词,理由一大堆。回忆这件事,华从柏挺得意:“不好管理,但她就服我,只有我去叫才行。”华从柏的秘诀是,给她讲道理,和风细雨地讲:“村里这么多人,你也后面来,他也后面来,田里的活就干不完。生产搞不好,大家就吃不饱。”没想到那位妇女听进去了,从此每天安安稳稳去出工,不再拖延推脱。别看只是一个小组长,作用可大了,如今仍在为山乡水利作贡献的龙山水库、开坑水库,便是华从柏领着村民们共同出力修筑的。
此后的几十年,华从柏始终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任何难办的事,只要组织开了口,他都倾力支持。2013年,华屋实施统一房改,很多村民舍不得将老房子拆除。华从柏心想,党员要带头,于是第一个站出来主动申请,推倒了自己的老房子。他深信组织说到做到,重新在老宅基地上建起新居。事实也的确如此,村里在集中连片民居的北面选了一块地,专门建造了一栋保障房,提供给五保户居住。房子位于蛤蟆岭下,地势略高,视线开阔,可谓站得高,望得远。由于华从柏腿脚不灵便,村里将他们夫妻俩安置在一楼住,方便进出。打开入户门,里面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现在,华从柏夫妻俩享受着政府兜底保障,以华从柏的话来说,那就是“吃公家,穿公家,住公家的”。他说,现在的生活,还多亏了结对帮扶干部的悉心照料,没有儿子,却好像多了许多个子女。他如数家珍道:“现在的党员干部,和我们那时候一样,好着呢。经常来看我,问家里有没有需要帮忙的。看到灯光暗了,就买新灯泡换,还不肯收我的钱。电视声音不响了,又叫师傅来修。有时候,还叫上一帮人来家里搞卫生,弄得清清爽爽的。”
我和华从柏一起算了一笔账,现在,华从柏每月可以领到五保金615元,老党员补助100元,高龄补贴100元,刘桃秀每月有低保金515元,高龄补贴100元,夫妻二人每年有17160元的补助收入,而且,各种补助的标准几乎每年都在提高。住房是免费的,看病最少可以报销九成,剩下的就是吃穿用度了。
正在我们说话的当儿,家庭医生来为两位老人检查身体了。医生为华从柏量完血压,乐呵呵地对他说:“血压很正常,身体好着呢。”
华从柏满心的欢喜都写在了脸上:“感谢共产党,我活了90多岁,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这辈子,跟党走,真是走对了。”
好日子,会来的
从众多气派的小洋楼中找到华割禾的家时,他正坐在门口的竹椅上笑眯眯地数钱。一百、两百,一十、二十……快活又满足的笑意从他黧黑的脸上荡开去,形成一圈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的涟漪。原来,他刚刚从市场卖菜回来,一下子进账四五百元。
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大门口,那是他专门用来运菜的。“现在一个月可以卖一万多元,苦瓜最好卖。”华割禾心情愉快,情不自禁对我说起了生意经。
别看华割禾现在笑容满面,其实,他是经历过贫穷和苦痛的人。
抬起头,我看见正门上方,钉有一块“光荣烈属”的牌匾。1952年出生的华割禾是一名地道的红军后代。爷爷华钦伦长征出发离开家乡时,华割禾的父亲华崇全才两岁。后来,爷爷华钦伦在长征途中壮烈牺牲,奶奶便带着唯一的儿子与华钦伦的兄弟并成一家,共同生活。奶奶操持家务,做饭洗衣,华钦伦的兄弟则租田种地,承担起了庇护孤儿寡母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后,华崇全做了十多年生产队长,在华屋小有声望。他结婚后,接连生下华割禾7个兄弟。
如果不是家中突遭变故,华割禾一家一向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1997年,儿子突然查出患有尿毒症。这对华割禾夫妇而言,如五雷轰顶。那是他们唯一的儿子,才20岁呀,人生才刚刚起头。夫妻俩决定,砸锅卖铁也要救治他。2000年,终于等到肾源的华割禾夫妇,四处借钱,筹集了20多万元,让儿子进行手术。然而,强烈的排异反应,儿子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术后一个多月,年仅23岁的儿子去世。
“就像天都塌下来了。”华割禾提及这段往事,不堪回首。那几年,他们给儿子治病的钱全是借的,满含悲苦地送别了儿子,又背下几十万元的巨债。
华割禾夫妇发誓要把债还清,他们决定种菜卖。那时候没有大棚,靠天吃饭,产量低。妻子谢二娣在家养母猪,养母牛,等猪和牛产了仔拉到市场上卖,一点一点地清偿着债务。只是这样的努力和天价的债务比起来,真是杯水车薪。最艰难的时候,他们总是互相打气:“好日子,一定会来的。”
果然,他们迎来了脱贫攻坚政策。
2014年,华割禾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干部来了,脱贫政策也来了。村里建好了大棚蔬菜基地,自动灌溉等基础设施全都做好了。村党支部书记找到华割禾,说:“你欠了那么多债,去种大棚菜吧。租金不贵,每年每亩700元。”华割禾能吃苦,他租下四亩多地,顺应着季节的变化和百姓的需求,将菜地种得满满当当。黄瓜、豆角、茄子、辣椒、葫芦……什么好卖种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菜地第一年就丰产丰收,每天能出三四百斤菜。加上有邮政统一收购,都不用自己去市场卖,价钱也按合同给得高。当年,华割禾种菜的纯收入达四五万元,于2015年成功脱贫。
夫妻俩尝到了甜头,更加有劲头。政府经常请专家来进行技术指导,华割禾越种越有经验。他说:“种菜不算累,种好了只要淋点肥,大棚蔬菜不会长虫子,不用打药,灌溉又有机械设备,我们只需要上午去割菜,下午打好包就行。”
稳定可持续的经济收入,让华割禾很是满足:“感谢党和政府,帮了我们的大忙。”
对华割禾而言,帮大忙的事还在后头呢。2018年,华割禾突发结肠破裂,住进了医院,他心里害怕极了,家里本来还有债务没还清,这一生病,不是又回到原点了吗?做手术前,他的女婿凑了6万元带到赣州,准备把钱交给医院,医生却告诉他,不用交。直到手术做完,他们都没有花一分钱。原来,按照贫困户医保政策,他享受先治病后结算的优待。最后结账时,华割禾担心地问医生花了多少钱,医生反倒安慰他说:“卡里余额还很足,你就放心吧。”
2019年7月,华割禾遵照医生的叮嘱再次来到赣州,进行第二次手术。20多万元的手术费,最后结算下来,他自己只花了2万多元。现在,华割禾已经痊愈,又生龙活虎地忙碌在大棚蔬菜地里。他感慨万千地说:“党的政策好啊,要不是政府,哪里医得好?卖屋都不够。”
如今,69岁的华割禾还在勤勤恳恳地种菜,67岁的妻子谢二娣大多数时候一起种,农闲时就到华嬷嬷蔬菜基地摘黄瓜,一年也能增加几千元的收入。他们的小女儿在外务工,挣了钱就交给父母。一家人的日子是越过越舒心,越过越红火。
小康路,美梦圆
正午的日色时明时暗地映照在乡间大地上,空气有一些闷热,华水林停止了田间的活计,走到高大宽阔的华屋祠堂来。祠堂里的烈士名录里,有华水林的爷爷华钦材。作为一名红军后代,1966年出生的华水林,从没有见过爷爷。
1934年10月,华钦材随红军北上,他的妻子是挺着大肚子送走他的。大约40天之后,华崇祁出生。“那时,我们家里只剩下太婆和奶奶两个大人,父亲是爷爷留下的唯一独苗。”华水林说,红军转移后,国民党反扑过来,对红军家属进行各种镇压,所幸华屋的老百姓非常团结,华崇祁在全村人的护佑下,长大成人了。
成年后的华崇祁接连生下了华水林六兄妹。孩子多,热闹是热闹,可是家里穷,只有两间半土坯房。等华水林六兄妹长大后各自成家,老房子已经容不下他们一起住了。他们只好各自外出打工,结了婚的拖家带口租房住,过年也只能轮流回家过,一家人生生创下了16年没有在一起吃过团年饭的纪录。
华水林的经历更是坎坷,在外奔波几十年,一直居无定所。“我开始在赣州租房住,跑了七八年摩的,帮人送货,打零工,后来回瑞金踏了三四年的三轮车,当搬运工挣点钱。有时在深圳,有时在会昌,有时又到了汕头……”多年的流浪,华水林已经很难准确回忆起在各地打工的先后顺序或时长了,他和妻子把两个女儿寄养在孩子外婆家,自己到处租房。
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是华水林做梦都在想的事。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新房梦还真的一朝实现了。2015年春节,华水林一家搬进梦寐以求的一栋小洋楼里,几十年的漂泊史彻底结束。
事情还得从2012年开始说起,这一年,按照国家建设新农村的政策,华屋开始筹办统一拆迁建房。理事会征求村民意见,需要房子的先报名,华水林听说一栋房子要掏12万元左右,他想,就是借钱欠债也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2014年9月份正式抓阄分房,那一天,华水林起了个大早,激动得手都打抖。无数次在梦中相遇的房子,如今就摆在眼前,66栋方方正正的三层小楼,哪一栋的户型设计、外观和楼间距都一样,它们的大门无不朝着南方,周围所住的邻居无不是华姓的亲人。
2015年春节,华崇祁夫妇、华水林一家,还有他们的兄弟姐妹与家属,16年来第一次在华屋的新房里欢天喜地过了一个团圆年。自然,此后的每一年,他们都可以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了。这个红军后代的家庭,如今已是四代同堂,全家有29口人。87岁的华崇祁和85岁的老伴,身体都还硬朗。尤其让华崇祁骄傲的是,他们家已经有了9个大学生,2个研究生。提起这些,老人脸上绽开了花,不迭声地说:“感谢党,教育得好。”
曾经四处漂泊、一身疲惫的华水林,如今真正回归家乡,不仅没有失去谋生的饭碗,反而走上了致富的道路。2015年3月,华水林在村委会的帮助下,租了8亩大棚,加上自己的2亩,种上了苦瓜、黄瓜、辣椒、豆角、黄芽白、上海青等应季蔬菜。第一年,华水林采下的蔬菜就卖了8万多元,除去投资,余纯利四五万元。
华水林是一个有种植理想的人。“我什么都想尝试一下。”他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是的,除了蔬菜,华水林还种瓜果,什么番石榴、小西红柿、百香果、芭乐、杨桃、菠萝、凤梨……各种时新水果,他都想种,还非种成功不可。他去福建、广东等地引进树苗,热带水果不好伺候,他就到处去学习技术。在一次次的现场指导中,他掌握了不少方法,再结合自己的经验,将10亩地侍弄得越来越好。
走进华水林的家,厅堂里堆满了瓜果蔬菜。偌大的屋子,楼上楼下,出入自在。想想从前逼仄的日子,简直天上地下。不仅如此,他们家还可以腾出4个房间用来做民宿,有团队客人来村里住宿时,村里会统一将客人分派到各家住,可以有100元一间的收入。他的大女儿在小学教书,每月也有三四千元的工资。在2020年的明白卡上,记载着华水林一家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万多元。
走在铺着青砖的华屋广场上,我注意到华水林打着一双赤脚。他笑呵呵地说:“赤脚好啊,有利于身体健康。”停了一会儿,他又对我道出肺腑之言:“从前是到处奔波,整天发愁没事做,怕挣不到钱。现在呢,安居乐业,每天过得很充实,只担心事情做不完。”
多么好啊,一双赤脚,连接着令人安心的地气;一个四处漂泊的人,终于把脚跟紧紧地扎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同为红军后代,华从柏、华割禾和华水林的故事远不是华屋的全部。今天的华屋,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社区建设示范点”“生态秀美乡村”“文明村镇”,华屋村民,小康生活梦圆。
何止如此呢,整个黄沙村,整个赣南,整个中国大地,都发生着沧桑巨变。如今,在黄沙村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长着4000箱蜜蜂,200亩白莲,200亩香芋,200亩油茶……他们用革命的干劲,发展产业,成立合作社,建立电商基地。
守得云开见月明。曾经的华屋很红,如今的华屋很绿。环村庄行走,注目,我看到更多美好的事情在这片热土上开枝散叶,映衬着人们郁郁葱葱的新生活。